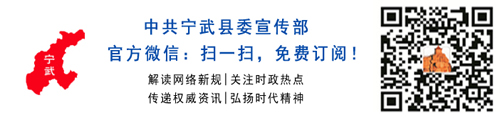前几年为写一本旅游方面的书,在宁武县住了一段时间。宁武人好客,吃饭总有人陪,本桌子上的人要喝酒,碰上熟人,其它桌子上的也要过来敬酒,差不多是每饭必醉,一喝一个酩酊。酒一喝多,饭就吃得少,酒醒后,肚子里空得慌,晚上常一个人泡了方便面吃。
一天,同村人在宁武县委工作的兔兔过来看我,听我说喝酒喝得肚子空,便说,今天不喝酒了,我引你去街上吃宁武特色。我问宁武有什么特色小吃,他说,最好的是黄菜馍馍。一听馍馍,我大摇其头,说,兔兔,吃面或者吃莜面吧,我吃饭最怕吃蒸馍馒头。兔兔笑说,黄菜馍馍不是馍馍,它叫馍馍,其实是饺子,你吃了就知道了,和咱们那里的大肚饺子差不多,很好吃的……
一听有大肚饺子吃,我顿时咽下口水,感到一种即将有的充实感。大肚饺子实惠,巴掌大一个,有两三个就撑你个肚儿圆。
“大肚饺子”是我家乡的一种“土吃”。在我印象中,吃大肚饺子总是在春天,而且总是和野菜联系在一起——我们这一代家在农村的人,童年、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生命,恐怕少有不和野菜联系的。在三年困难时期,我们曾重做了一次神农,差不多把所有的野菜都尝遍了,所以,我有这种印象应该是确实的。
大肚饺子的面是高粱面、馅是野菜和土豆丝混合的馅。具体做法是:高粱面用开水和起,擀成一个个碗口大的饺子皮,皮的厚薄和碗的厚薄差不多,包上馅后将碗反过来扣在饺子合口处一摁,便齐齐地切成一个半圆,然后在铁锅里烫,这烫是纯粹的干烫,因为不搁丁点儿的油,烫到两面都焦黄时,里面的馅也就熟了。趁热吃,皮儿松脆爽口,馅儿新鲜有味,从地里劳动回来,吃上几个大肚饺子,解饿解乏。
我吃过的大肚饺子大多是小蒜馅。小蒜就是野生的蒜,瘦瘦弱弱的叶、玲玲珑珑的蒜,叶有五六寸高,蒜有黄豆或蚕豆大。生腌了吃,辣辣的,有股介乎于蒜和韭菜之间的味儿,做馅蒸熟后,却没有韭菜和蒜苗的味重,淡淡的清香,是野菜独有的那种清香。小蒜作为野菜的时间很短暂:“二月半,挑小蒜。”农历二月半左右,雁来之后,燕子来之前,地里最早的野草萌生了,十分稀少,却十分醒眼,这萌生最早的野草里就有小蒜,在春天酥松的耕地里绒绒地闪着绿。我在六七岁时便被奶奶差遣着挑小蒜了,小蒜挑回来后总要吃一顿大肚饺子。挑小蒜的时间有半个月左右,长大后的小蒜就不好吃了,我们家乡的人说一过清明,小蒜就被燕子擦了屁股了,所以,清明节以后的小蒜便没人再挑来吃了。传说自然只是传说,我小时就怀疑过,小蒜那样多,燕子毕竟有限,有限少的燕子怎么能将可以说是无限多的小蒜都擦了屁股呢。而且,它又为什么要那样去做?除非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吃。事实是过了清明以后,小蒜的叶不再是嫩叶,吃起来既不好咬嚼,味道也很难闻,谁还再稀罕吃它呢?
宁武的黄菜馍馍和我原平老家的大肚饺子只是形似和做法相同,其余的风马牛不相及。大肚饺子的皮儿是高粱面,黄菜馍馍的皮儿是莜麦面;大肚饺子的馅儿是野菜,黄菜馍馍的馅是酸菜。不过,黄菜馍馍确实好吃,一是它的皮儿,它的皮儿莜面里掺着蒸熟后的土豆泥,吃起来软和得多,馅的酸菜里也和着土豆,酸酸的别有风味。兔兔那次叫我出去,我一顿吃了七八个黄菜馍馍(一个一两左右),肚子饱了还想吃。以后,常常一个人跑到街上去吃,而且见了外地来人,便向他们介绍宁武的黄菜馍馍。后来,宾馆招待贵客时也上黄菜馍馍了,却不知是否受了我的影响。
黄菜馍馍虽然好吃,宁武人的叫法我却总认为不够妥切。首先叫馍馍让人莫名其妙:有包馅的馍馍吗?馍馍有扁的吗?馍馍都是蒸的,有烫的吗?其次是馅的叫法也不妥:馅明明是酸菜,酸菜与黄菜两回事,黄菜是晒干了的萝卜缨子,那叫黄菜,酸菜是盐腌水渍了萝卜缨子,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,混为一谈总让人不大舒服。不过,反过来说,我这说法大概也会让宁武人不舒服:你说我们黄菜馍馍叫得不对,我们还说你那大肚饺子叫得不对呢,有那么大的饺子吗?饺子有水饺、蒸饺,有烫饺吗?
编辑:闫凤婷